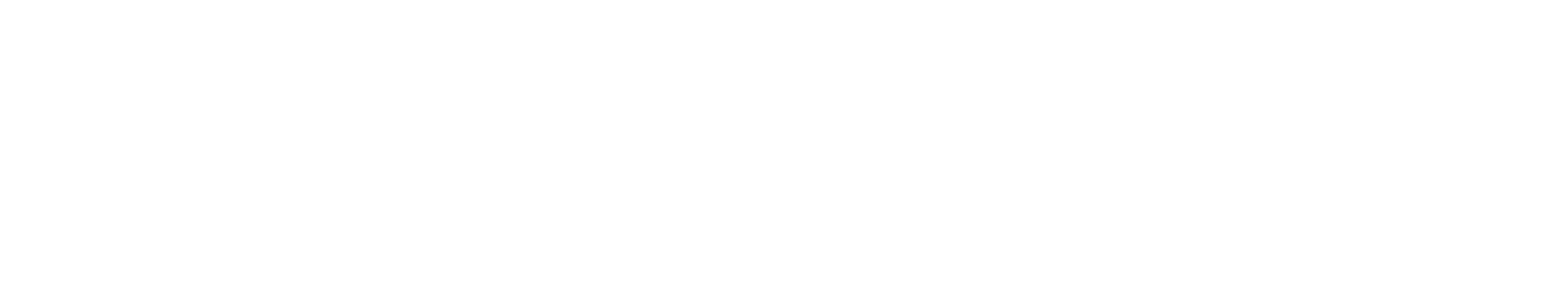电机系微信公众号
校友微信公众号
研究生微信公众号
本科生微信二维码
北京院微信公众号
四川院微信公众号
校友工作
- 校友通讯
-
班级介绍
- 1955级发0班
- 1960级电607&电61班
- 1961级高71班
- 1973级发3班
- 1974级电4班
- 1976级发6班
- 1976级高6班
- 1978级高8班
- 1979级发9班
- 1979级高9班
- 1979级电9班
- 1980级高0班
- 1980级电0班
- 1981级发11班
- 1981级发12班
- 1981级电1班
- 1982级高2班
- 1982级电2班
- 1983级发32班
- 1984级发42班
- 1984级高4班
- 1984级生医4班
- 1985级发51班
- 1985级发52班
- 1985级高5班
- 1985级电5班
- 1985级生医5班
- 1986级发61班
- 1986级发62班
- 1986级高6班
- 1986级电6班
- 1986级生医6班
- 1987级发71班
- 1987级发72班
- 1987级高7班
- 1987级电7班
- 1987级生医7班
- 1988级发81班
- 1988级发82班
- 1988级高8班
- 1988级电8班
- 1988级生医8班
- 1988级电专51班
- 1989级电91班
- 1989级电92班
- 1989级电93班
- 1989级生医9班
- 1989级电研89班
- 1990级电01班
- 1990级电02班
- 1990级电04班
- 1991级电11班
- 1991级电12班
- 1991级电13班
- 1991级电14班
- 1991级生医1班
- 1992级电23班
- 1992级电24班
- 1992级电研1992班
- 1993级电32班
- 1993级电33班
- 1993级电专9班
- 1995级电研5班
- 1995级电专11班
- 1996级电研6班
- 1996级电61班
- 1996级电62班
- 1996级电63班
- 1996级电专6班
- 1997级电71班
- 1997级电72班
- 1997级电73班
- 1997级电74班
- 1997级生医7班
- 1998级电82班
- 1998级电博8班
- 1999级电92班
- 1999级电博9班
- 2001级电11班
- 2002级电21班
- 2002级电22班
- 2002级电23班
- 2002级电24班
- 2003级电31班
- 2004级电42班
- 2005级电51班
- 2006级电61班
- 2006级电64班
- 2007级电博07班
- 2013级电34班
- 2014级电43班
- 历年教职工
 1979级高9班
1979级高9班
班级简介:
1979年入学,1984年毕业,学制五年。班级人数34人,其中男生31人,女生3人。平均年龄为17岁,来自全国12个省市。
住宿情况:
男生住:一号楼;女生住:新斋。
班级格言及由来:
为学求高,为人愿久。
电机系的系训“为学在严,为人要正”来自于朱镕基学长在电机系六十周年系庆时给电机系的来信,高九班对电机系学弟学妹们的寄语,我也想从为学与为人两方面来凝练,还要兼顾具有高九班的特色。
为学自然是要求得高深学问,而且学无止境,需要不断探求,所以说“为学求高”;为人从高九班四十多年的同学情感来看,肯定是愿意长长久久,友谊地久天长,“日久见人心”,几十年都认可的朋友是真朋友,另一层含义自然是希望老同学们都健康长久,所以用了“为人愿久”。
求和愿都是寄托希望的用词,用在寄语上也算合适,高九也直接含在寄语中了。
班级故事:
我的同学 我的班
清华大学电机系高九班梁曦东
我第一次对校庆日校友返校留下深刻印象的,要算1981年清华建校七十周年的那次。工字厅前的纪念石“清芬挺秀,华夏增辉”就是81年校庆立的。我们那时觉得毕业三十年返校是最自豪、最风光的事,但是很遥远、很遥远。老校友们胸前的红色名签上,最吸引人的莫过于19XX的那一行。
如今,我们也毕业三十年了!随着毕业聚会的脚步一天天临近,三十年前的往事一幕幕浮现脑海。一个个或清晰或模糊的零碎片段,在回忆中逐渐聚拢。学校的大环境对每一位同学的成长无疑十分重要,但是班里的小环境、宿舍的局部氛围对同学的影响也同样显著,给大家留下的印象绝对深刻。
1.我们宿舍不起眼的“约法三章”
我们班共34位英雄好汉、巾帼须眉,来自全国12个省市,平均17岁,男女生比例31:3。男生住在一号楼,女生住在新斋。
我和刘益东、沈威、张键、胡文堂、林斌、李平芳七人入学时住在朝北的346,后来班内南北互换时搬到了朝南但只能住六人的349,李平芳没有过来。346是一个大房间,四张上下铺以外,中间有几张大桌,足够我们七人同时看书、写作业。因此我们一开始都是在宿舍上自习,反正对学校的教室也不熟悉。好在刚入学,大家都老实。慢慢的,大家也就习惯在宿舍上自习了。晚饭后七人安安静静地看书写作业,有互相讨论的,也都小声说话。其他宿舍的同学来聊天,一看七人规规矩矩看书的架势,立马就知难而退了。这样不知不觉形成了我们宿舍的第一个约定:晚饭后宿舍是自习的地方,不能大声喧哗。在宿舍上自习的习惯坚持了将近一年,到大学二年级我们才分散到教室自习。在宿舍自习的效率虽然不会高过在教室,但是将近一年的坚持,对我们树立良好习惯无疑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记得制图课我们全班一共6位同学期末成绩优秀,其中5位在我们宿舍。
第二个约定:宿舍不是打牌的地方,谁要想打扑克牌另外找地方。这是跟着第一个约定而来的,这个约定伴随了我们整整五年,不管是在346还是在349。那时没有网络,刚入学也没电视,打牌是最普遍的娱乐活动,到高年级有些同学与时俱进,开始打桥牌。但是不在宿舍打牌的约定我们一直坚持下去了,包括周末。大二以后虽然在宿舍自习的人很少了,但我们宿舍一直是比较安静的。
第三个约定是关于文明用语的,说话不能带脏字。当时跟七字班、八字班相比,九字班刚入学就是一帮孩子,说话带脏字比较普遍。记不得是谁在哪天卧谈会上提议:说话不能带脏字。结果一呼群应,并定下规矩,谁在宿舍说话带一次脏字,罚款一个钢蹦儿(记不得几分了),而且找来一个玻璃的罐头瓶,立即执行。一开始大家还不太适应,但随着罚款数额的增加,脏字明显减少,不到一个学期,想罚谁的款就太难了。包括吵架,也是“文明争执”,不许骂人。
这个“约法三章”当时并没有什么“顶层设计”,是我们自己逐渐形成的,虽然都很不起眼,但对我们每个人的影响绝对不小,而且效果持久。这三十年中,我也多次跟我的学生们说起班级乃至宿舍局部环境的重要性。
2.在“工程师的摇篮”里成长
清华过去一直以“工程师的摇篮”而自豪,我们入学时,大红横幅上也写着:“欢迎你,未来的工程师”,可是并非每位进入清华的学生都愿意成为或适合成为工程师。
79年入学时,我们系还叫“电力工程系”,我们专业是“高电压技术与设备”。在很多外人的印象中,这专业名称听着就吓人。入学不久的一天傍晚,班主任杨学昌老师说带我们去高电压实验室参观。参观了什么现在完全记不得了,只记得全班在高压试验厅的铁丝网外站好后,听说要加高压了,只见试验区里一道闪光,伴随着一声巨响,象打雷,然后又重复了几次。现在看来,当时施加的电压应该在三十万伏左右。这肯定是我们第一次见识高压放电。后来上专业课,还有老师说,高电压不危险,“全国每年触电的,几乎都是220伏低电压的”。好在班里没听说谁被吓着不敢学了。
当时大家对挑专业不太敏感,觉得只要进了清华,学哪个专业都可以,不象后来那么讲究。可是来自黑龙江的沈威不一样,他是有艺术天分的,绘画极好,后来想转建筑系。记得他提交的有素描好几张,给大家印象最深的是一幅一米高的油画作品。在349宿舍一笔一笔,画的爱因斯坦跟画报上的一模一样。那是我第一次见人画油画,真的把我们这些“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我们很庆幸他没转成,那时转系真的很不容易。沈威的外形也很有艺术气质,接近一米九的大个子,我们班的两座珠穆朗玛峰之一(另一座是来自吉林的杨海军),说起话来从来不紧不慢,轻声细气的,一副好听的男中音,后来参加了学校合唱团。沈威似乎从不跟人急,这可能部分地出于保护嗓子的需要,我就没听他说话超过50分贝的,而且语速从来只有我的四分之三。
北京来的刘益东是我们班唯一的高压二代。他来到高九班,应该是他老爹选择的。可是他压根儿就不喜欢工科,有点进错了“摇篮”的感觉。可是人家虽然不喜欢,但依然硬着头皮在八年中拿下了高电压的工学学士、工学硕士,只不过在最后还是义无反顾地主动跟高电压“绝缘”了。
班主任杨老师无数次地强调,学高压的人数学一定要好。我们班数学最好的要数来自辽宁的王百宽和来自江苏的许国祥了。王百宽是好几年的学习委员,许国祥简直就是高九班的“文徵明”,那一手小楷般的钢笔字写的极为规整。一直到刚毕业的《高九通讯》,我写好了发刊词,都还是请许国祥抄录后才复印给大家的。有一年暑假,我们两个去卢沟桥,见到了乾隆皇上的“卢沟晓月”碑,但是以我们二人的细心,在卢沟桥上走了一个来回,还是没数清楚有多少石狮子。
那时的任课教师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不少。比如教高等数学的盛祥耀老师,讲课不用看讲义,整黑板的公式推导,外加精确到小数点后好几位的计算结果,从来是一笔写下来不带犹豫的,让我们佩服得不得了。专业课里面印象深的教师就更多了,比如教电机学的李发海老师、教高电压绝缘的薛家麒老师、教高电压技术的陈秉中老师、教过电压的高玉明老师、教高压开关的张节容老师、带我们西安实习的吉嘉琴、王昌长老师。李发海老师的电机学讲得特别生动,跟工程应用结合的很多。记得期中考试,我和王百宽考了一百分,李发海老师为鼓励大家,说谁期末再考一百,总评就给一百。结果期末我又考了一百,李老师也果然兑现诺言。能在电机系的几门“硬课”中拿到一个满分真不容易,其他几门专业课,再也没听说谁拿到一百分了。
“工程师的摇篮”并非只有工科的课程、工科的知识。改革开放的风气吹遍全国,清华这座得风气之先的殿堂当然更有条件邀请到社会各界名流学者来举办讲座。胡松华在大礼堂的一曲“从草原来到天安门广场”,让我们这些从小听惯了“革命歌曲”和样板戏的孩子第一次领略了歌唱艺术的魅力;刘德海几次来清华,他演奏的“春江花月夜”、“十面埋伏”、“飞花点翠”等名曲令人过耳不忘;钱绍武来清华讲雕塑;李苦禅大师的得意弟子来讲国画;聂卫平也不止一次来清华讲解围棋。清华的各种讲座对大家绝对是意外之喜,犹如春风化雨。学校提供各种氛围,能从中汲取多少养分,看你自己的。
3.三人行,必有我师
上苍把这34颗聪明的脑袋瓜放在一个集体中,一定有他的道理。每人都有他的长处,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学会欣赏他人的优点,并且互相学习。孔老夫子很早就明白这其中的道理,曰:三人行必有我师。孟子他娘也明白这个的道理,所以三迁,挑人。
刘益东虽然对工科不感兴趣,他对人文社会科学等其他方面可是偏爱有加,自学起来孜孜不倦。各种社科类讲座他比我听的多,说起来萨特、尼采、普利高津、朦胧诗等一套一套的。张键则对“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情有独钟,一再向我们推荐:“现代的工程师如果不懂“三论”是完全不合格的”。林斌对外国小说兴趣浓厚。胡文堂看书的用眼卫生习惯绝对不好,可是人家怎么看都不近视,真让人“羡慕嫉妒恨”。有一天我在三院上自习时,在桌上看到哪位清华高手刻下一副上联:“近世进士尽是近视”,印象深刻,可惜多年未见满意的下联。
入学不久,我买到一本《唐诗三百首》,对中国古典文学产生了兴趣,后来在全校选修课时,我和刘益东都选了《中国古代史》。《论语》、《老子》、《孙子兵法》是我曾经向同学们推荐的中国文化最简洁的读本。从通史和文学、哲学、美学等专门史的角度看,从围棋、太极拳等不同的应用角度去体会。不知不觉中,我体会了搭建适合自己的知识结构的重要性。有了史学的基本构架,其他各方面的内容可以相对容易地拼装进来,容易理解,也容易记得住。这就好比有了检索系统的图书馆,知识就容易被存储、被调用。另外,有了中国文化的底子,再去看西方文化,也容易对照学习、对照记忆。
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兴趣方向,但是经常的交流、讨论、介绍、辩论,使得我们又在自己的兴趣之外涉猎了不少其他同学的方向。比如第三次浪潮、大趋势、李约瑟难题等共同关注的话题。这样一个互相学习、互相督促、互相鞭策的环境远不是自己在家一个人自学所能比的。
沈威音乐、绘画很棒,我们跟着欣赏;张键像模像样地练习书法,我们其他几人也买来颜柳欧苏的字帖。可是轮到自己写的时候,总感觉学颜真卿时,写出来的象一堆肥肉,学柳公权时,写出来似一堆软绳。由此深深感慨理解性学习和动作性学习的完全不同。
申沛泽是我们班男生的老大哥,性格果断、脾气火爆。五年大学我们班就只有他一位班长。李东担任了五年的组织委员。李庆余是五年的生活委员,勤勤恳恳为大家服务,毕业时他是唯一外地生直接留京的,全班没有二话。毕业设计的某一天,高压实验室楼外变压器突然起火,虞育号毫不犹豫,拎起灭火器就跟老师们一起灭火。
王永勇是典型的小资,对戴望舒的雨巷、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念念不忘,完全没有来自黑龙江的东北汉子的样子。张伟东的小提琴演奏,一亮相就立马征服了全班。赵建平的眼镜片永远那么“朦胧”,似乎永远在进行哲学思考。杨海军绝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喜欢逗乐,且能言善搅,无论何人何事,嘴皮子上都不会输。除了高电压操作规程以外,他大概从来没有把任何外加的要求放在眼里。那些约束别人的规定,在他眼里都是“龟腚”。钱中民看国外小说手不释卷,刘益东赠送雅号“钱大公子”。毕业前考研究生时,班里不少人报考了。可是就在考研的第二天早晨,杨海军叫他起床去考试。他居然因睡意正浓,把被子往头上一蒙,继续睡,不去考了。真是举重若轻,潇洒如此,没有辜负“钱大公子”的雅号。
姜小英、任艾棣和李雯靖是我们班“珍贵而重要的”半边天,在男生粮票不够吃的时候,二话不说慷慨解囊。那些年的清华男生,应该都对女生的支援十分难忘。我们班女生让男生难忘的还有另一方面,三位女生来自京津,年龄比男生大一些,说起话来就有一副大姐姐教训小弟弟的派头。以至于毕业留言时,还有某女生在某男生的留言册上写下“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这样令人终生难忘的经典句子。
4.为了能健康工作五十年
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是每位清华学子不懈追求的标杆,如今三十年已过,我们完成了60%,及格了。基础课、专业课的学习情景,很多人在多年后都记不清了,但是班里体育活动的珍贵镜头,不管经过多少年,大家都记忆犹新。
踢足球是不少清华男生的经常性项目,认识的一块踢、不认识的也掺呼进去踢。我们班最大型的体育活动,就是朝南宿舍和朝北宿舍的男生踢“南北大战”,一次就需要上场22人,还不算替补,绝对是普及型的“群众运动”。自己班踢完了还要跟其他班踢。可是天有不测风云,班长申沛泽就在与外班的一次比赛中,咔嚓一声巨响,腿断了。好在打上石膏几个月后痊愈了。
大三体育课,王永勇硬拉着我去选修武术。武术课结束后,我留在武术队学习太极拳,83年和84年参加首都高校武术邀请赛,均有奖牌斩获,为学校和高九班争了光。太极拳也成为我多年的健身项目,成为我从清华学到的终生受用的本领之一。
我们班体育最拿得出手的还是要数半边天姜小英,人家在娘胎里就会打球。姜小英作为清华乒乓球女队的主力,打了五年的北京高校乒乓球锦标赛。单打、双打、混双、团体,奖牌拿到手软,绝对是我们班的骄傲。
三十年前的夏天,我们毕业了。高九班入学34人,毕业获学位34人,人数一样,人头也一样,十分整齐利索。大家完整地完成了学业,带着各自从学校、从老师、从班级、从宿舍、从同学那里学来的本领走向五湖四海。
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无比怀念我可爱的同学、难忘的班。